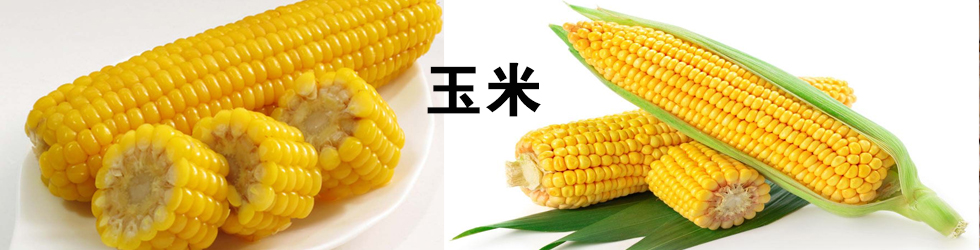初秋的风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每年的这个时节我总会感冒——大概是因为在我这副躯体里,夏天还不想走,而秋天又来得急的缘故吧!
都说秋凉之际,正是思人之时,我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格外地想念我的外婆——年的那个秋天,我的外婆因为肺癌去世了。
外婆是一个很纯粹的庄稼人,乡下私房门口的那片一亩三分地是她日常生活的全部。因为家庭的特殊关系,我并不是很经常去外婆那里探望,但只要我去,第一眼看见的永远都是那个在田垄间忙碌的身影。
“阿婆!”,我喊她。
“诶,来啦!”,她笑笑。
这,就是我自打记事开始,和外婆打招呼的方式——没有过多的寒暄用词,因为我知道田里的农活耽误不得!
孙儿辈的到来,永远是老人家的心头热。农活忙完的外婆自然是要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的:菜市场买的烤鸭、叉烧之类的熟食、自家田里摘的新鲜蔬菜、当然还有后院鸡窝里的三颗鸡蛋——对,不多不少,每次只要三颗。
“阿婆,今天中午吃蛋炒饭吧!”
“嗷,两个鸡蛋够不够?留一个煎荷包蛋?”
“好!”
蛋炒饭配荷包蛋是我来外婆家吃饭雷打不动的主食,外婆会做的菜有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蛋炒饭和荷包蛋。
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我却乐意呆在旁边欣赏。外婆做蛋炒饭有着一套独门的手艺,起锅烧油后,将隔夜饭倒入锅里面,快速地翻动后会听到“噼噼啪啪”类似于炸饭的声音,觑着眼睛瞧还能看到许多油星子飞溅到外婆的手上。
“阿婆,你手痛吗?”,我有些好奇。
外婆没说话,眼睛只是盯着锅里不断翻动的饭。等到饭被炒得有些糊香味的时候,外婆将它单独盛了出来,紧接着就下入之前打好的鸡蛋——这是很重要的时刻!
在鸡蛋液还没完全成型的时候,将先前炒好的饭倒进去,用锅铲将它们翻炒均匀,至于程度嘛,自然就是争取让每一粒米饭都包裹上鸡蛋液。
当然,临出锅前,自然也是要点缀上一些红火腿和绿葱花的。
而我吃这一碗蛋炒饭也有一套独有的方式:
首先是闻。刚出锅的蛋炒饭有着一股浓郁的糊香味,这是我记忆尤深的关键——外婆总说“蛋炒饭有糊香味才算是有烟火气息的”。
我明白,庄稼人对于“烟火气”是有着天生的执着的,我的外婆更是如此。小时候我经常缠着她让她讲过去艰难岁月的故事,而这些也是我下饭的“佐菜”。
在那个饥荒年代,能有一口饭吃是极为不易的事情,外婆一家人最常吃的是一种类似于炒面的东西,玉米苞子粉混合上其他的粗粮一起炒香,因为缺乏调味品,只能用糊香来代替——这大概就是外婆做的饭总有一股糊香味的原因吧。
其次是吃。蛋炒饭得趁热吃,可趁热吃又会烫嘴,于是的方式就是用筷子从碗的边沿用类似于打圈的方式将米饭送入口中——扑鼻的香味瞬间转化为了口腹的满足,妙哉!
趁我吃饭的功夫,剩下的一枚鸡蛋就会被外婆用来煎荷包蛋——这大概是我吃的鸡蛋种类了,只是外婆过世以后,我再也没能吃上记忆中的荷包蛋了。
和蛋炒饭一样,外婆的荷包蛋也是烟火气息的,这主要来源于被煎的焦脆的边缘。
洗干净的锅热锅下油,外婆手里的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一溜胶质状的东西顺着锅边滑到了热油里面,随后就是一阵热烈的“噼噼啪啪”——说实在的,我不太忍心看荷包蛋煎制的过程,总觉得柔嫩的鸡蛋被放入多度的热油里是一件略显残忍的事情。
但它终究是好吃的!
薄薄脆脆的外沿是第一种层次的口感,略带焦香气息;绵柔的蛋白是种层次的口感,以抚慰被前一阵焦脆咯得微微发疼的舌头;最后是洒满椒盐的蛋黄,如果能吃到流心的,口感自然又要上升一个级别了。
然而,不到想吃得熬不住的时候,我是不会自己去做这两样餐食的,原因在于:我不喜欢被鸡蛋爆裂而产生的油星子溅到我手上的感觉——或者说,我讨厌一切突如其来的厄运。
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体比我还强壮的外婆会患上肺癌这种疾病!
被病痛折磨了一年半之后,外婆在那个深秋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早上我接到妈妈的
“外婆....走了...”
一时之间,我竟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如鲠在喉——那是我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次归家了,从公里外的苏州到外婆的灵前,只用了2个小时。
一整场葬礼,我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躺在冰棺里的外婆,耳边似是又回想起了外婆卧病时对我的嘱咐:
“阿婆走了...你不要太难过啊...”
这一刻,我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