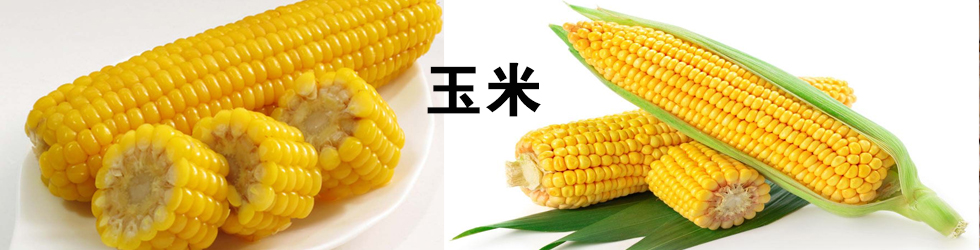在我的故乡,人们常常把玉米又称为苞谷。金灿灿丰收的玉米棒子,常常被人们一串串吊在屋檐下,依靠太阳和风,晾晒干。
在我小的时候,晚上常常一家人坐在一大堆被晒干的,堆成山的玉米棒旁边,在庞大的圆簸里,一边聊天,一边用手剥下一粒粒的玉米颗粒,剥完一个玉米棒子,最后只剩下一大堆玉米芯子。常常把剥完的玉米芯子,堆积起来烧火做饭。
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删除在每年三月下旬育下玉米种子,旁边施好肥。一场透雨下来,玉米苗微笑着蹭蹭的往上长。田间地头,山野坡地,玉米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是整装待发的士兵攻山,从低处慢慢涌向高处。稚嫩的枝茎,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充满着向上的力量。三片,五片,七片玉米已经半人深,一片绿油油的,延展在山野,延展在农人们的心里,钩织着农人们喜悦的心情。
一直以来,我对玉米情有独钟,玉米没有大米那么高贵,没有小麦那么受北方人的欢迎。它的枝干高大,株株如剑,直指苍穹。在玉米成熟的季节里,掰下玉米棒子,砍下杆子可以吃甘蔗,甜甜的汁液没有纯粹的甘蔗那么甜,但在物资匮乏的时代里成了人们的最爱。
在那个年代里,苞谷成了人们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顿苞谷稀饭。把水添好,放入磨碎的苞谷渣子,锅烧开,在放入切好的红薯块,一锅的苞谷稀饭便成型。没有小菜,常常把腌制好的浆水菜,放入盐,调料,竟然能吃几大碗。端午前后土豆成熟,刮成丝放苞谷面,在参入一点面粉,热锅倒油将搅和好的面糊倒入锅,摊薄,香喷喷的苞谷面馍做好,惹得我们常常围在锅边等吃。
冬天里,人们常常为来年的玉米地,而忙碌准备。一家人忙碌的在坡地里,挖窝,灌上稀粪,盖上干粪,在盖上泥土。等到来年三月育下种子,等到玉米苗长两三片叶子的时候,薅草,施肥,间苗。苞谷的生长过程至少要薅三,四道草。每次都是艰辛的劳动。父亲常常顶着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忙碌在玉米地里锄草。因此,我们也常常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删除从小我们和玉米为伴,常常想起来带给我们无尽的乐趣。秋天里,上坡放牛,我们一群孩子钻到玉米地里,挑看红色皮的玉米杆,折断当甘蔗吃,我们称为“甜杆子”。多年以后,当我们吃甘蔗时,常常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玉米杆。我们常常掰下嫩嫩的玉米棒子,放在火上烤熟,吃着黄愣愣,黑乎乎的玉米棒子,满嘴喷香,嘴巴被吃得黑黑的,末了,还把玉米须子粘在下巴,装扮成老爷爷,按照须颜色的深浅不同,分为等级。
我常常走在遍地结满硕果的玉米地里,结实饱满的玉米棒子挂在一株株的玉米杆上,童年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历历在目,久久不能散去。
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删除